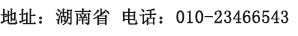No.西非冒险之旅编辑
郑艳琼
本期内容来自刘笑嘉新书《全世界给我勇气》,星旅行为合作伙伴。
年,刘笑嘉辞职独自去旅行,边走边写,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,反省自己对父母的爱的理解。她在路上给父母写信,最终获得了理解和支持。
她在这本新书中说:“在路上,我有了大块的时间用来回味平日里的生活,记忆仿佛将生活换了一副面孔。喧闹的通通快进,宁静的变为定格画面,真正震动心弦的俱无声无息,一帧一帧,逐格展现。也许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。只因最好的旅行,是通往自己的内心。”
这不仅仅是一次西非冒险之旅。
梦旅人/刘笑嘉,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,85后专栏作家、旅行达人,《汽车自驾游》、《游遍天下》等杂志撰稿人,“蚂蜂窝”驻站专栏作者。患多动症久未治愈,恶朝九晚五,好东跑西颠。做过记者、时装编辑、美容编辑、自由撰稿人、编剧、会展策划……最近的一份工作是旅行。出版作品《我怕没有机会,选择真正喜欢的生活》、《全世界给我勇气》。世界那么大,去哪儿撒撒野?
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聊,无聊到你无法忍受的地步,那么,除了把它变精彩,你别无选择。
五个月前,我说想找个花费不多、签证又不那么难办的地方旅行。有个闺蜜说,想旅行又嫌贵,要么等有钱了再去,要么干脆移民,换个护照,哪儿哪儿都能免签。
可地球那么大,干吗非扎堆儿去那些著名旅游胜地啊?找个游客少的地方不是什么难事。咱们从小到大,大拨轰的事情还嫌少吗?我就喜欢故意找人少的“歧途”走,就像我们的生活,为什么不找一条人少的路走呢?
欧洲太文艺,不够刺激;我那可怜的财力又不足以支撑我去南极、北极转一圈;姑娘我身体也不够壮硕,喜马拉雅山暂时还爬不了。把各种“斯坦”、海岛、东南亚想了一圈后,我把目光落在了非洲。于是,充满生命活力的非洲就成了我的不二之选。
有一种“夏娃理论”认为,如今地球上的各个人种,都是20万年前某一个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,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“夏娃”。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,迁徙扩散到欧洲、亚洲等地,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。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均来自这位非洲女性,她是人类各种族的共同祖先。虽然这种假设自问世以来,就不断遭到各种质疑。但我对于祖先、迁徙、故土这些词,天生痴迷。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区间看,我去非洲算作旅行。如果将时间的区间扩展到20万年前,按照“夏娃理论”的假设,我去非洲就可以算回老家了。
每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,我们的内心都会被新鲜感充满。可地球那么小,也许我们的祖先在这千万年的历史中,早已迁徙到它的每一个角落了。所以,无论我们到了哪里,都可以像回家一样舒心。
“我旅行是因为喜欢到处走动,我享受旅行给我的自由感觉,我很高兴摆脱羁绊、责任和义务,我喜爱未知事物;我结识一些奇人,他们给我片刻欢愉;我时常腻烦自己,以为借助旅行可以丰富个性,让我略有改观。我旅行一趟,回来的时候不会依然故我。”我不知该怎样形容毛姆这段话在我心中激起的波澜,它道出了旅行带给我的东西,这几乎是我想要的一切——满足好奇心、交朋识友、塑造更好的自己,最重要的是自由的感觉。
想要自由,总得舍弃点儿东西,比如“三安”——安定、安逸、安稳。我倒是不怎么反“三俗”,很喜欢反“三安”。在我心里,不要道听途说的人生比“三安”重要得多。
同样喜欢反“三安”的陆洋同学,听说我去的地方很有趣,于是决定同行。他是个沉默的观察者,用相机记录一路上的所见的人和事。习惯了独来独往的我,也不知带上他究竟是福是祸。
可地球又是那么大,姑娘你干吗不挑个舒坦点儿的地方?
我想用《托斯卡纳艳阳下》里的一段话回答:“为了自己想过的生活,勇于放弃一些东西。这个世界没有公正之处,你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计。若要自由,就得牺牲安全。若要闲散,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成就。若要愉悦,就无须计较身边人给予的态度。若要前行,就得离开你现在停留的地方。”
既然出来旅行,当年吹过的牛,迟早都要兑现的。因为在第一本书中夸下海口,说了要去非洲,弄得我不去就会很没面子。这种事情,我会随便说出来吗?哼,笑话!
本书摄影/陆洋,摩羯座工作狂。自幼学习绘画,北京服装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。擅长时装、名人纪实、婚礼纪实、旅行纪实等方面的拍摄,并建立YOUNG视觉影像机构。同时把自己分裂成平面设计师、首饰设计师、陶艺设计师、插画师、剪辑师及专业舞者。
他们说这里很危险
我的签证是传说中的“返签”,就是将自己的护照通过国际快递邮寄给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,获得返签证明后,再寄回我手上。所谓的返签证明不过是一张印着字的A4纸,我的护照上没有任何变动。在首都机场时,机场的边检人员看到我那极度简约的返签证明直犯嘀咕,反复确认我办理该证明的合法途径后才放行。最后还抛给我一个问题:“你确定到了塞拉利昂能够顺利入境吗?”我除了猛点头外,没法做别的反应。
我最佩服自己的就是健忘的本事。“万一到了塞拉利昂,不让我入境怎么办”这个问题,吃过第一顿飞机餐后,我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直到我真正到达了非洲,才知道“听说”有多么可怕。有关非洲的传闻,甚至连气候都是谣言,非洲不等于热死人。
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机。刚下飞机,我就忍不住哆嗦了一下,这里的夜晚跟北京一样冷。遇到一个黑人哥们儿和我一起转机,他反复找人问候机室和登机门号码,即使电子屏幕上明明清楚地显示了。总会有人比你还不淡定,跟着他们,自己就不用着急了。
出发前,我在网上能查到的有关塞拉利昂的信息都是“旧闻”,对于那边的具体情况与完全不知道只差两个字——基本不知道。在去加纳首都阿克拉的飞机上,遇到一位大哥,曾经在塞拉利昂住过七年之久,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实用信息,比如哪里有中国的医疗队,得了疟疾就要立刻往首都赶。毕竟待的时间久,这位大哥已经把疟疾看得和一到换季就会得的感冒一样普通。我心里还是很不安,因为自己十分招蚊子稀罕,朋友们都亲切地叫我“移动蚊香”,只要有我在身边,朋友们再也不用担心被蚊子咬了。
我还向这位大哥打听了一件传闻,大家都说在非洲有两样东西十分“好使”,过安检遇到麻烦或者想让黑人帮个忙,只要送对方一小瓶风油精或者一小盒清凉油,对方一定十分高兴。大哥说五六年前确实是这样,但是现在只有money(钱)好使。说话的同时,他还伸出右手的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,来回捻搓。
下飞机时,两位热情的黑人空姐拉住我问bye-bye(再见)用中文怎么说。学会以后,俩人现学现卖,一遍遍跟我说“再见”。真的会再见吗?旅行时每天认识的陌生人是平时生活中接触到的好几倍,可大多数人,我们耗尽今生,也无缘再见。
第二次转机时,遇到五个矿业工人,他们中的四个都是第一次去塞拉利昂,只有“带头大哥”在那边待过半年。“带头大哥”说当地没什么可玩的,无聊得很。他说那里蚊子多得要命,千万不要在天黑后洗澡,否则一定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,被咬了肯定得疟疾,准跑不了。他说得了疟疾浑身那个难受啊,一会儿冷、一会儿热,即使治好了,也会反复发作。他说那里抢劫、盗窃天天发生,物价还贼高。他说来这个国家绝对是你最错的决定。他说……
我开始怀疑飞机上那位大哥跟眼前这位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吗?
四五年前,人们都喜欢去京郊的爨底下村度周末。我听西画老师说,他发现比爨底下还近的地方,有个古村叫灵水举人村,爨底下过度商业化后,文艺青年和文艺中年们都去那里写生了。我找了个周末,背上吃的,坐上可以到达北京西边的地铁。出了地铁站,在等公交时,不断有开黑车的司机过来问我是不是去爨底下。当得到我要去灵水村的答案后,他们都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我,说那地方穷乡僻壤,在一座破山上,有什么可玩的。后来终于坐上公交车,就连同车的乘客、附近的村民也都说那地方根本不值得一去。可我确实在那个村子里度过了美好的一天,没有吵吵嚷嚷的游客,去哪儿都不用排队。我在村子里随意溜达,不管是古树还是破庙,走到哪儿高兴了,就坐下来写个生,还遇到村民热情地请我吃刚打下来的枣。
幸亏,无论到达的地方究竟是好是坏,都只是“他们说”的,那都是他们嘴里的塞拉利昂而已。我这种人,说难听了是不是叫“不到黄河不死心”?
我的毛病不止“死心眼”这一个,还有盲目乐观。关于旅行的计划只做一少半,一多半都未知岂不是更有趣?订旅店的时候,连着三家旅店的国际长途都打不通,我干脆决定不订了。“带头大哥”得知我没订旅店后,先是咋舌不已,然后告诉了我离码头最近的一家中国人开的旅店。天性盲目乐观的好处,除了想不起没到来的麻烦,还能获得热心人的帮助,一举两得。干吗非把所有未来的情况都幻想成问题?我们难道还嫌人生中的麻烦不够多吗?
飞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飞机是架小型飞机,机上没有空姐,全是空少。登机时,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黑人经过我身边,姿势特别正规地作了一个揖,说了声“你好”,脸上还带着调皮的笑容。这让我从那么多可怕的“他们说”中抽离出来,放松了不少。
随着转了两次飞机,机上黄皮肤的亚裔人种越来越少,我的心情反而越来越轻松,因为身边的黑人都十分有礼貌,充满善意。
下飞机后,排队等待入境,黑人通过海关都很顺利。到我时,小窗口里的黑人慢条斯理地翻看着我的返签证明和护照。
“你确定到了塞拉利昂能够顺利入境吗?”此时,首都机场边检人员的问题终于重新出现在我脑海里。在我幻想出第十种悲惨结局之前,窗口里的黑人兄弟终于将我的证件看腻了,慢悠悠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入境章。既然入境章都盖好了,看来我的返签证明没有问题,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
虽然手续已经办齐全,对方却不打算把护照痛快地还给我。他冲我伸出三个手指,不断来回捻搓着(看来这个表示钞票的手势真是全球通用),嘴里只有一个词不断重复——money。“带头大哥”早就提醒过我,机场的黑人们很喜欢向中国人索要小费,不需要理会。我假装听不懂,露出一脸疑惑的表情。于是这哥们儿开始施展自己的语言天赋,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,一个字正腔圆的“钱”字居然从他嘴里蹦了出来。可能是我错愕的表情太狰狞,他冲我使劲儿挤了挤眼睛,就把护照还给了我。
隆基机场建在一个半岛上,若想到达市区,需要先坐车到码头,然后转坐渡轮。在车上坐好后,一个瘦瘦的黑人姑娘站在车下送她的两个朋友上车。一向以黑妞自居的我,在这个西非国度里,变成白得扎眼的人。姑娘跟她的朋友聊了几句以后,就开始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微笑着回应她的目光。她施施然走到我座位的窗口,靠在车边,柔声介绍自己叫阿佳,说她很喜欢我的眼睛,问我从哪里来。汽车发动时,她伸手在我的手上轻轻握了一下,然后挥手向我告别。
短短相处的这几分钟,让我对这个国家的人充满了好感,即使刚才那个贪婪的海关人员,在我脑海里也被自动过滤得只剩下了狡黠。
码头边有个小小的咖啡馆,里面坐了几个人,悠闲地喝着咖啡,欣赏着大西洋上的夕阳,顺便等船来。
为了体会乘风破浪的感觉,我挑了和船长并排的座位。等待开船的时候,我仔细打量着他,衬衫被他的肤色衬得雪白。船长发现我一直盯着他看,突然转过头冲我猛抛媚眼,吓得我赶紧收回了目光。船员发出乘客已满可以开船的提示后,他立刻收敛笑容,正襟危坐,熟练地操作起来。
远处的弗里敦,仿佛随着船身,在大西洋中上下起伏。市区的灯火伴着夜幕与咸咸的海风,一起扑面而来。
天黑后,船靠了岸。我们按照“带头大哥”的指点,找到那家中国人开的小旅店。他说晚上在弗里敦街头走路十分危险,因为随时可能出现黑人骑摩托车抢劫。所幸,旅店离码头很近,快些走过去,没有什么情况发生。可是每次身后传来摩托车的声音,我都会紧张地回头看。
我和旅店的老板娘丽姐求证当地飞车抢劫是否高发,她说自己和在这儿认识的中国人都没遇到过,但她在集市上曾经被黑人抢过包,她一大声呼救,周围卖东西和买东西的当地人立刻堵住了劫匪,把那人狠狠揍了一顿。她旅店里有过黑人员工偷客人钱的事情发生,被她发现后死不承认,其他员工还互相包庇,都被她开除了。看来当地人和黎叔的价值取向很接近:最烦打劫的,一点儿“技术”含量都没有。
后来的日子里,随着对弗里敦越来越熟悉,我发觉当地治安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,晚上去小卖部给手机充值,饿了去买烤肉,去黎巴嫩人开的超市,或者跟附近的居民们聊天、唱歌、跳舞,都是很安全的。
点击视频,亲历西非
星旅行by
郑艳琼